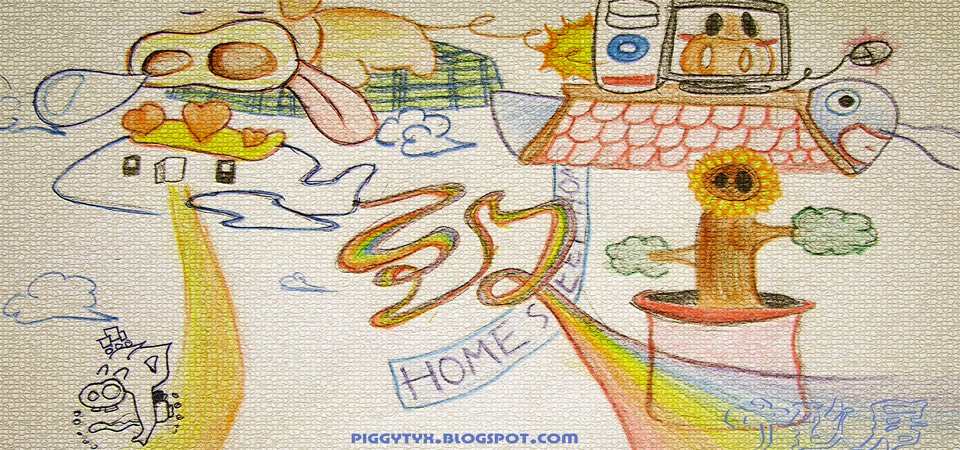昨天把《玫瑰的名字》落在办公室里,今天拎起背包,忽觉好轻盈,少了那份巨细,靡遗。
从蔡厝港搭地铁到布莱德,多少个站,多少时光,右手不安地握着手机,拇指摩挲在键盘上,今天阅读的董桥,那些故人往事,轻轨构成另一座桥。
偶然抬起头,远方一座熟悉的棕色古堡,开阔得好像荒漠飞沙,扬声器亲切地说了声兀兰,回过神来,脚底下是一行行的棕榈夹道,却闻不到南洋的椰语蕉香。
古堡如此威壮,以往总是在它脚下虔诚地仰望,驱车在它身旁绕了千百回,一次都不曾侵踏,仿佛根本不属于这个城,害怕会坠入无底的迷惘。一座山是一座城,古堡四周凌乱地发芽。
列车继续遄行,经过一面湖泊,原来是入海口的瓜拉。石头堆砌的堤道以及平整的草坪,有人在垂钓,钓一个下午的闲情,仿佛有海水流了进来。水面上鲜艳的浮标。
海的那端,住着倔强的可爱的娃,下定决心一股脑埋头就做了,没想太多,从不顾及后果。好了,错了,傻傻一笑就顺势改了过来,也不想再去深究了。海的这端。
列车钻入黑冷冷的隧道,打开门,硬生生拆断阅读的桥。
31 October 2010
25 October 2010
牛油小生报道:数据人生
烟霾的影响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什么事都能与烟雾扯上关系:能见度低要注意开车啦,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啦,旅游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啦等等,仿佛无烟不起浪。
相关当局为我们划出指标,PSI一旦超过100点,就当属危险水平,仿佛很有道理,但转念一想,101点很“危险”,那么99点却显得“适中”了吗?数据作为一种指标,把我们推向临界点的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观感正来自我们身处的标签世界,资本社会的基础模式——品牌与标价为我们标示出的品质的数据化差异。
天空忽降甘霖,赶紧拧开电视、网络咨询,一声惊叹:“哇,指数终于降低了!”仿佛大家都已忘了呼吸。
一谈起数据,不少人首先会联想起股票、经济,但其实它无处不在,比方说总警察署每年公布的犯罪率报告,其实与政府每年颁布的财政报告没有差别,本质上就是要利用数字来说明结果,来检验是非对错。
本月份,警方逮捕了3名连环非礼案的色狼,还公开通缉一名干案11年之久的“心跳色狼”。报道说,2010上半年的非礼案件,与去年同时期相比,攀升了11%。这种数据的上升,真叫人担心,不禁让人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小生请教了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给的答案完全出乎意料,其中一人说:“案件的上升并不意味罪犯的增加。”
的确,一个人能够干下许多案子,总体分析,社会并没有制造出更多色狼,而是社会没能够有效制止同一个色狼一次又一次地犯错。另一位专家则告诉我,数据上升或许是因为有更多受害者愿意坦诚面对类似事件主动报案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对类似事件更加包容的关系,不再认为受害者是可耻、道德错误的。
哦,人们宁愿选择相信专家。
前些日子,有一系列关于一位新加坡留学剑桥的学生在伦敦遇车祸的新闻,从《早报》到《新明》、《晚报》,当然还有《海峡》、《新报》,大家好像总是一副很关心的样子,却似乎中了某种魔咒,坠入对数字的怵目迷恋以及暴力滥觞。
《早报》说:“被拖行1.2公里”;《晚报》、《新明》异口同声“1.6公里”;《海峡》、《新报》最引人注目,醒目的标题大写“Dragged 2KM”,这便是数目字带来的暴力想象——让我们的联想力驰骋,并以公里计算——多么漫长的暴力。
社会的教育机制以及生活风格,要求所有人敏感于数字,仿佛数目越大就越了不起(考试100分就很了不起,这便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这起意外新闻大概报道了10天,本应该在重复时删去暴力的语词,却没想到,这些距离与里数,却成为新闻的辨识点。人们认得的仅仅是那血腥的数字,怜悯变得面目全非。
“妈的,都磨成什么样了,这样子拖。”大概不少人会这么想。
或许数目字小一些,人们的关注便不会那么显著。数据充斥我们的生活与记忆,潜移默化地形成我们进行判断的凭据。
小生怀疑这与电脑化的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每天对着电脑,浏览色彩斑斓的图像以及密密麻麻的资讯,却忘了这些影像的基础是一串串“1010”的符号。我们不自觉地透过数字符号来阅读信息,从而以同样的方式来阅读世界。(那么那些不看电脑却依然对数字迷信的人们呢?说到底,人们已然中毒千年。)
“我凝视着你的脸:你有两道眉毛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对耳朵一张嘴,一个也没少,当真是一种叫作人类的动物。”
相关当局为我们划出指标,PSI一旦超过100点,就当属危险水平,仿佛很有道理,但转念一想,101点很“危险”,那么99点却显得“适中”了吗?数据作为一种指标,把我们推向临界点的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观感正来自我们身处的标签世界,资本社会的基础模式——品牌与标价为我们标示出的品质的数据化差异。
天空忽降甘霖,赶紧拧开电视、网络咨询,一声惊叹:“哇,指数终于降低了!”仿佛大家都已忘了呼吸。
一谈起数据,不少人首先会联想起股票、经济,但其实它无处不在,比方说总警察署每年公布的犯罪率报告,其实与政府每年颁布的财政报告没有差别,本质上就是要利用数字来说明结果,来检验是非对错。
本月份,警方逮捕了3名连环非礼案的色狼,还公开通缉一名干案11年之久的“心跳色狼”。报道说,2010上半年的非礼案件,与去年同时期相比,攀升了11%。这种数据的上升,真叫人担心,不禁让人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小生请教了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给的答案完全出乎意料,其中一人说:“案件的上升并不意味罪犯的增加。”
的确,一个人能够干下许多案子,总体分析,社会并没有制造出更多色狼,而是社会没能够有效制止同一个色狼一次又一次地犯错。另一位专家则告诉我,数据上升或许是因为有更多受害者愿意坦诚面对类似事件主动报案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对类似事件更加包容的关系,不再认为受害者是可耻、道德错误的。
哦,人们宁愿选择相信专家。
前些日子,有一系列关于一位新加坡留学剑桥的学生在伦敦遇车祸的新闻,从《早报》到《新明》、《晚报》,当然还有《海峡》、《新报》,大家好像总是一副很关心的样子,却似乎中了某种魔咒,坠入对数字的怵目迷恋以及暴力滥觞。
《早报》说:“被拖行1.2公里”;《晚报》、《新明》异口同声“1.6公里”;《海峡》、《新报》最引人注目,醒目的标题大写“Dragged 2KM”,这便是数目字带来的暴力想象——让我们的联想力驰骋,并以公里计算——多么漫长的暴力。
社会的教育机制以及生活风格,要求所有人敏感于数字,仿佛数目越大就越了不起(考试100分就很了不起,这便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这起意外新闻大概报道了10天,本应该在重复时删去暴力的语词,却没想到,这些距离与里数,却成为新闻的辨识点。人们认得的仅仅是那血腥的数字,怜悯变得面目全非。
“妈的,都磨成什么样了,这样子拖。”大概不少人会这么想。
或许数目字小一些,人们的关注便不会那么显著。数据充斥我们的生活与记忆,潜移默化地形成我们进行判断的凭据。
小生怀疑这与电脑化的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每天对着电脑,浏览色彩斑斓的图像以及密密麻麻的资讯,却忘了这些影像的基础是一串串“1010”的符号。我们不自觉地透过数字符号来阅读信息,从而以同样的方式来阅读世界。(那么那些不看电脑却依然对数字迷信的人们呢?说到底,人们已然中毒千年。)
“我凝视着你的脸:你有两道眉毛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对耳朵一张嘴,一个也没少,当真是一种叫作人类的动物。”
21 October 2010
我不懂得保留
走在那部巨轮的感受,其实心底明白自己是多么幸运,牺牲的实在太少太少。
如果知是一种表现,那无知又何伤大雅,但巨轮仍需要前进的动力,因此每天都必须认真地表现得有知,每一句表达都不需要负太多责任,恍惚间飘逝,遗忘成为最好的解药。
列车把囚徒真空包装输送到一个又一个终站,阅读过的那种感受总与实际体会发生错位,人们摩肩接踵,顾不得尴尬,尊严在那一秒钟丧尽,让思绪驰骋,列车的顶却压得太低,灵魂在头上盘旋,在那狭窄的空间互相穿过彼此,纠结在一起,终究没有交流,恨不得一辈子不再见面——没关系,我并不会记住你,再次见面时,你已是另一个新的陌生的你——再见的不再见。
歌声在四方盒子中来回折射,一个人发出一百万种回声,宣泄成团忘了吸气,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大家瞬息疯了,以为挑选了九十九首迥异的曲目,却被伴奏带魂牵梦萦,彼此做着稳妥的梦,即便牵手也没有心的触动。
欢声笑语之后,文字与文字终究要离你而去,即便这是你的所有,它总能在上一秒便离你而去,但轮子的旋转让你晕眩,仿佛能够追逐,抑或产生下一次的那极为相似的幻觉,那便足够,足够去留守一辈子。
如果知是一种表现,那无知又何伤大雅,但巨轮仍需要前进的动力,因此每天都必须认真地表现得有知,每一句表达都不需要负太多责任,恍惚间飘逝,遗忘成为最好的解药。
列车把囚徒真空包装输送到一个又一个终站,阅读过的那种感受总与实际体会发生错位,人们摩肩接踵,顾不得尴尬,尊严在那一秒钟丧尽,让思绪驰骋,列车的顶却压得太低,灵魂在头上盘旋,在那狭窄的空间互相穿过彼此,纠结在一起,终究没有交流,恨不得一辈子不再见面——没关系,我并不会记住你,再次见面时,你已是另一个新的陌生的你——再见的不再见。
歌声在四方盒子中来回折射,一个人发出一百万种回声,宣泄成团忘了吸气,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大家瞬息疯了,以为挑选了九十九首迥异的曲目,却被伴奏带魂牵梦萦,彼此做着稳妥的梦,即便牵手也没有心的触动。
欢声笑语之后,文字与文字终究要离你而去,即便这是你的所有,它总能在上一秒便离你而去,但轮子的旋转让你晕眩,仿佛能够追逐,抑或产生下一次的那极为相似的幻觉,那便足够,足够去留守一辈子。
18 October 2010
三菜一汤
明知道是不可逆转的现实,依旧随波逐流地跟从,迈步的过程越是充满疑惑,越是艰辛。倘若怀抱一股突破现状的愿景,可能终究只能逃向镜子深处,慢慢被吞噬,直到被遗忘。回返的时候,把一些什么落在那里,那个深处。
星期天的下午,拎着环保袋响应来自绿色的声音,即使它有可能又是一次骗局,但至少被骗得服服贴贴。人们总是用谎言来拆穿谎言,没有留下一点退路,潮汐涨落,留下来的成为真理,不知道哪一天又要被拆穿。但至少,心智的认知已然诚服,秉着那股真挚,又何来亵渎。超市的账单标签上一毛钱的折扣,便是天理昭彰的馈赠。
烧饭煮菜是件快乐的事,这句白得不能再白的话。把不同色泽味道的食材混出一种新滋味,无论多少次都令人振奋不已,毕竟那种比例以及氛围,不可能如此精准地与前一次或下一次形如一体。一锅汤不好好搅拌,也和不了那层次的区别。这次选择一条白萝卜搭上一条胡萝卜,料不到竟被抢着染成了红色,喝起来十足老黄瓜汤的风味,倒也罢了,甜滋滋的,滋润爽喉,图个快乐而已。
失去了火候概念的电磁炉至少还能够闷出一碟菠菜,切许多许多蒜头,为着贵客的一句话,却恰如其分地辛香怡人,不让菜色单调,蚝油调得再咸一些可能就坏了一桌子的味道。咖喱中加上鸡翼,纯粹是为了让鸡肉咖喱包装酱成为鸡肉咖喱料理,马铃薯好像是个必然。炒菜便是稳当地跟着逻辑走,八九不离十,偶尔出点小意外小惊喜而已,只要不搞糊了,嚼嚼嚼稀巴烂下肚就是。为什么不能加番茄?怕酸。
最后炒个蛋。遇到瓶颈就,炒个蛋。
收拾整齐送走了客人才发现忘了拍照。人们已然习惯相片对记忆的攫取,无论上一秒发生了什么事,倒数的钟声总能亲切地引导嘴角的上扬,还有一些快乐的手势。“不能上facebook炫耀了——”多么教人沮丧,一开始便放弃了被一千万双眼珠子浏览的机会,放弃了那些平面的文字表达,以及大拇指的方向。未来,或许那些回应都将被视频替代,正如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被新的理所当然的东西给取代,除了那种匿名偷窥的快感,但总有办法的,时代在轮转。未来?谁晓得。
咖喱的辣味依旧荡气回肠,平淡的星期天傍晚一边吃家常菜一边出汗,细微地粘附在额头发际,没能够坠下,忽而被吸收了,被擦拭去,抑或是蒸散消逝,调整风扇的角度,有点远,风的触手淡薄得窒息。边吃边说话的饭桌习俗,哪怕是绿意嵌在齿缝间,还是满口碎肉碎饭,不发一语一定会让菜凉去。于是出的汗。
每道菜的分量还算拿捏得当,就剩下一些饭,等着明天被回锅翻炒。饭后用一部电影来消磨时光,几个人坐着一起阅读某个记忆片段,虽说是消磨,但却足够创造出更多的话题,作为维系你我的丝絮。或许能够创造出一个迷宫来方便你我迷路,也许可以让它一望无际一无所有,漫步在虚无慢慢迷失,直到那个深处。透过半部电影勾起一千部电影的类似情景,让它们互相抵消直到空无。明知道结果,却依旧义无返顾地步入那个终结,于是不满足,于是去寻找下一部电影,再让它慢慢勾起回忆,勾起的同时创造出更多今天与明天。
小生试了一口汤,与记忆中的滋味相去甚远。
星期天的下午,拎着环保袋响应来自绿色的声音,即使它有可能又是一次骗局,但至少被骗得服服贴贴。人们总是用谎言来拆穿谎言,没有留下一点退路,潮汐涨落,留下来的成为真理,不知道哪一天又要被拆穿。但至少,心智的认知已然诚服,秉着那股真挚,又何来亵渎。超市的账单标签上一毛钱的折扣,便是天理昭彰的馈赠。
烧饭煮菜是件快乐的事,这句白得不能再白的话。把不同色泽味道的食材混出一种新滋味,无论多少次都令人振奋不已,毕竟那种比例以及氛围,不可能如此精准地与前一次或下一次形如一体。一锅汤不好好搅拌,也和不了那层次的区别。这次选择一条白萝卜搭上一条胡萝卜,料不到竟被抢着染成了红色,喝起来十足老黄瓜汤的风味,倒也罢了,甜滋滋的,滋润爽喉,图个快乐而已。
失去了火候概念的电磁炉至少还能够闷出一碟菠菜,切许多许多蒜头,为着贵客的一句话,却恰如其分地辛香怡人,不让菜色单调,蚝油调得再咸一些可能就坏了一桌子的味道。咖喱中加上鸡翼,纯粹是为了让鸡肉咖喱包装酱成为鸡肉咖喱料理,马铃薯好像是个必然。炒菜便是稳当地跟着逻辑走,八九不离十,偶尔出点小意外小惊喜而已,只要不搞糊了,嚼嚼嚼稀巴烂下肚就是。为什么不能加番茄?怕酸。
最后炒个蛋。遇到瓶颈就,炒个蛋。
收拾整齐送走了客人才发现忘了拍照。人们已然习惯相片对记忆的攫取,无论上一秒发生了什么事,倒数的钟声总能亲切地引导嘴角的上扬,还有一些快乐的手势。“不能上facebook炫耀了——”多么教人沮丧,一开始便放弃了被一千万双眼珠子浏览的机会,放弃了那些平面的文字表达,以及大拇指的方向。未来,或许那些回应都将被视频替代,正如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被新的理所当然的东西给取代,除了那种匿名偷窥的快感,但总有办法的,时代在轮转。未来?谁晓得。
咖喱的辣味依旧荡气回肠,平淡的星期天傍晚一边吃家常菜一边出汗,细微地粘附在额头发际,没能够坠下,忽而被吸收了,被擦拭去,抑或是蒸散消逝,调整风扇的角度,有点远,风的触手淡薄得窒息。边吃边说话的饭桌习俗,哪怕是绿意嵌在齿缝间,还是满口碎肉碎饭,不发一语一定会让菜凉去。于是出的汗。
每道菜的分量还算拿捏得当,就剩下一些饭,等着明天被回锅翻炒。饭后用一部电影来消磨时光,几个人坐着一起阅读某个记忆片段,虽说是消磨,但却足够创造出更多的话题,作为维系你我的丝絮。或许能够创造出一个迷宫来方便你我迷路,也许可以让它一望无际一无所有,漫步在虚无慢慢迷失,直到那个深处。透过半部电影勾起一千部电影的类似情景,让它们互相抵消直到空无。明知道结果,却依旧义无返顾地步入那个终结,于是不满足,于是去寻找下一部电影,再让它慢慢勾起回忆,勾起的同时创造出更多今天与明天。
小生试了一口汤,与记忆中的滋味相去甚远。
17 October 2010
从那天开始的吧
能端说小生持球时候的眼神很飘,“你好像在怕什么?”
英式女篮,小生嫌少触及,第一次玩就要参加公司比赛。中文报派出4男4女,上阵必须是3男4女,毕竟这是女篮,女生没得休息。女篮禁接触,容易走步犯规,裁判哨声频频,大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最终还是侥幸获得季军,意外的是竟然有一些奖品,煞是丰厚,本来就只是一把滥竽,荒腔走调地吹着。
司职中场的时候,小生失魂落魄。“你还没有睡醒啊?”队友发狠骂道,忽而传了一记远吊,小生会错意反身接球,痴痴望着球飞出场外。
专心。许久不记得专心,仿佛突然失意了的一种本能。小生在场上沉默异常,其实在足球场上、篮球场上,自己便是那么孤僻,一句话不说,总以为队友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沟通,最基础的是言语,小生忘记了,总以为是心。但是心又飞去了哪里?
中学时代,在场上球技一般却总是装作老大,对队友呼呼喝喝,满腔自信,长大后渐渐隐去的这种本能,似乎枯灯殆尽,最后一点微光幻化成轻烟飘散,像离魄背弃中心的逃逸。
还是跑一百米算了,与跑道沟通思绪,短短的十几秒钟足够去思考很多很多,然后没有必要让人家知道,知道了也没有一点关系。
英式女篮,小生嫌少触及,第一次玩就要参加公司比赛。中文报派出4男4女,上阵必须是3男4女,毕竟这是女篮,女生没得休息。女篮禁接触,容易走步犯规,裁判哨声频频,大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最终还是侥幸获得季军,意外的是竟然有一些奖品,煞是丰厚,本来就只是一把滥竽,荒腔走调地吹着。
司职中场的时候,小生失魂落魄。“你还没有睡醒啊?”队友发狠骂道,忽而传了一记远吊,小生会错意反身接球,痴痴望着球飞出场外。
专心。许久不记得专心,仿佛突然失意了的一种本能。小生在场上沉默异常,其实在足球场上、篮球场上,自己便是那么孤僻,一句话不说,总以为队友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沟通,最基础的是言语,小生忘记了,总以为是心。但是心又飞去了哪里?
中学时代,在场上球技一般却总是装作老大,对队友呼呼喝喝,满腔自信,长大后渐渐隐去的这种本能,似乎枯灯殆尽,最后一点微光幻化成轻烟飘散,像离魄背弃中心的逃逸。
还是跑一百米算了,与跑道沟通思绪,短短的十几秒钟足够去思考很多很多,然后没有必要让人家知道,知道了也没有一点关系。
14 October 2010
满月酒的那夜,月如钩
工作的第一个月,那种嗷嗷待哺的日子,以菜鸟之名搪塞。满月后,已不容许太多的娇嗔,一切理应变得更专业一些,但依旧深藏着某种期盼——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有时依然忍不住要贯彻那种幼稚的想法。
在殓尸房外,咨询认领遗体的亲属时,那种不知所措并没有骤减。很唐突的一句“请问你是来办手续的吗”,从僵硬的嘴角钻出——当然更多时候是躲在后边默默地听,真想一睹自己的表情。那种场合轻松不下来,生离死别,恒古的命途与情绪,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尽,亦不是一轮哭诉所能教人体悟的。
工作后有一股股翻腾的发牢骚欲望,文字变得激昂,绽放却朵朵苍白,那不是小生所追寻的,花。城市需要一个热衷于跳飞机的女孩,因此西西拉着裙脚荡漾,飘忽的凌波微步,看不见脸庞却认得出那微笑。小生暂居的这座城,要如何与之发生联系?始终无法将精力汇聚在岛屿的一颦一笑。捧着心头,眺望海峡的大块姑娘。
创作文字的各种形态,当初义无返顾地抉择,却未能适应那种体裁的标准。仿佛只有那种惯式是正确的。新闻头要一览无遗地呐喊出全文要点,精简而准确。素日太追求华丽,而今必须坦荡荡拨开外衣时,却显得狼狈。人生是爬满跳蚤的华丽大衣,忍着恒痒拼命遮掩那些抓痕与疮疤。习惯于躲藏,终于忘记了最简单的语调。
那种稚气与这种简单到底怎么了?是结构,抑或是内涵?幼稚的华丽的袒露。世故的平实的暗笑。
工作的第一个月,几次偷闲回到熟悉的新山,那些零星的高楼,以及敞开的视野,虽然少了绿意,空气依旧开阔爽朗,管他那些拥堵的车子的臭屁汩汩地氤氲凝集。流汗,挥舞羽毛球拍,高吊、抽杀,脑海中尽是电视上高手过招的影像。谁来送一本秘籍,神掌如来,让羽毛洁白的画道刁钻有劲道,一如颜真卿的书贴般稳当,一旦逮到机会便化身张旭狂草落风沙。这种艺术想象不着边际地越驰越遥,混身臭湿却总是够那球不着,巴巴望着铩羽的彗星陨坠球场。
还有歌唱。心里一直奢望能够工作歌唱游刃两岸,有时忽然懒劲一发,便嵌在沙发上不肯动弹一下。终于来到团室,听几曲合唱,开声后各部正式配搭。多次缺席,平时又不曾恶补,盯着豆芽字的升幂降序虽然有点荒腔走板,但心情却出奇舒畅,没有一点积压。
回家早已不是必然的终点,难得归去,为的却总是另一些忙碌,仅仅将余温留在那床熟悉的漩涡中,却被次日清晨的风扇,摇晃中卷走,剩下狼藉的梦呓与皱褶。父亲踩着油门,让低档吃力地咆哮,久久不肯推进档牙。总是无语的车厢,播放着不知名的交响乐曲子,那天夜里父亲特地来到关卡迎接,难得的谈话却引来无言的凌乱,那些曲子仿佛电影配乐,教车子的氛围更加无法逆转。父亲想避开堵塞的大道,尽量绕远路走,拐弯抹角的路程不知道是否节省了时间。
回到家,大家陆续入房睡觉,把一盏盏灯都熄掉,唯剩狭廊那最后那一点灯光,是深夜家中唯一不灭的照耀。夜半梦醒,想撒一泡尿,想啜一口水,便循着灯塔般的指引,一步步踏去。夜夜如斯。
11 October 2010
中产阶级万岁
小生有时候会故意在报道中隐射一些现实,因此那些文章都没能见报,但小生依然愿意那么做,那是自己应付的责任。小生热衷的课题也往往与编辑逻辑的兴趣没能达成共识,但能够书写自己的兴趣,依旧是件快乐的事。
上星期有幸能够采访NUS举办的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个课题就非常有趣,探讨的是普遍人们对“人口贩卖”的刻板印象。许多国家机构通过宣传把贩卖人口的受害者凝聚成被迫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与儿童,其实这是一种男性观点的结果。事实上,有半数的贩卖人口行为,涉及劳动力的贩卖,许多从事苦力行业的男女便被排除在这种论述之外。
小生说过,巨型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政治机构默许这些劳动力的进入,却拒绝提供任何福利与保护,把他们囚禁在隔离空间里,用中国话说是“眼不见为净”,制造城市稳定与安逸的假象。
可以说,道德因素造成色情行业与劳力工业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关注点。扫黄行动,作为一种道德象征,大大提升国家机构的正面形象,以一种男性视野凝造“拯救妇孺”的假象,而不受舆论关注的其他面向,便暴力地被排除在外,继续存在,继续被剥削。这或许是许多国家机构刻意而为之的策略。
研讨会还提到,贩卖人口的个人因素,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被绑架到工地或色情场所的。不少人出自对城市的憧憬而“选择”了这些工作,同时并不排除有“被蒙骗”的可能性,但人口贩卖的源头,必也有值得人们去深思的课题。
或许,新马华人的祖先大多属于“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因此为了不伤及人民的自尊心,这些劳力贩卖问题,便在舆论中变得不受重视。
小生在报道中特意注明了新加坡仍未签署联合国人口贩卖议定书这一条事实,还刻意删除了“马来西亚于2009年终于签署”的一句话,已经给予充分的颜面了,却仍由于“版面不足”而无法见报。今天有一篇关于外劳被雇主非法禁锢的事件,上星期的研讨会内容不正好作为注脚来提高大家对类似事件的认知吗?
题外话。星期五警方发出文告,要求协助寻找两起车祸的目击证人,因为是文告,所以简单处理,由于版面拮据,又被搁置。昨天到殓尸房的时候,发现其中一起车祸的骑士抢救无效过世了,内心有种谴责,好像没能做到一件该做的事,因此很想把这篇报道好好完成,无奈再次落版。
不幸丧生的青年是小生同乡,每天穿行长堤往返工作,还有一些令人感伤的巧合。小生不愿意解释为,受害者是外籍工人所以报道才被割爱。小生宁可相信这是因为《晚报》、《新明》已抢先报道了,造成失去新闻价值,才会被搁置一旁。现实终是残酷。
星期五还采访了一位青少年问题辅导员,缘因一则学生被偷拍到性爱短片的风波。老经验的摄影记者在一旁为两只菜鸟补充疑问,引发很多新的思考。类似事件,小生认为,无论多想责备这所学校的风气也好,都不应该过于注重性与当事人的身份。他们终须面对未来,那么做太不人道,尤其当他们都还是未成年孩子的时候。
经过几番周折,报道被要求悬置,小生认为是件好事。记者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发掘故事以提供娱乐?排列咨询来教育民众?还是寓教于乐?应该更多揭露上层社会的黑暗?还是去挖掘小人物的自卑心灵?
报章如果一直呈现上层结构的风光面貌,读者到底会氤氲出怎样的思维?中产阶级万岁。
上星期有幸能够采访NUS举办的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个课题就非常有趣,探讨的是普遍人们对“人口贩卖”的刻板印象。许多国家机构通过宣传把贩卖人口的受害者凝聚成被迫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与儿童,其实这是一种男性观点的结果。事实上,有半数的贩卖人口行为,涉及劳动力的贩卖,许多从事苦力行业的男女便被排除在这种论述之外。
小生说过,巨型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政治机构默许这些劳动力的进入,却拒绝提供任何福利与保护,把他们囚禁在隔离空间里,用中国话说是“眼不见为净”,制造城市稳定与安逸的假象。
可以说,道德因素造成色情行业与劳力工业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关注点。扫黄行动,作为一种道德象征,大大提升国家机构的正面形象,以一种男性视野凝造“拯救妇孺”的假象,而不受舆论关注的其他面向,便暴力地被排除在外,继续存在,继续被剥削。这或许是许多国家机构刻意而为之的策略。
研讨会还提到,贩卖人口的个人因素,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被绑架到工地或色情场所的。不少人出自对城市的憧憬而“选择”了这些工作,同时并不排除有“被蒙骗”的可能性,但人口贩卖的源头,必也有值得人们去深思的课题。
或许,新马华人的祖先大多属于“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因此为了不伤及人民的自尊心,这些劳力贩卖问题,便在舆论中变得不受重视。
小生在报道中特意注明了新加坡仍未签署联合国人口贩卖议定书这一条事实,还刻意删除了“马来西亚于2009年终于签署”的一句话,已经给予充分的颜面了,却仍由于“版面不足”而无法见报。今天有一篇关于外劳被雇主非法禁锢的事件,上星期的研讨会内容不正好作为注脚来提高大家对类似事件的认知吗?
题外话。星期五警方发出文告,要求协助寻找两起车祸的目击证人,因为是文告,所以简单处理,由于版面拮据,又被搁置。昨天到殓尸房的时候,发现其中一起车祸的骑士抢救无效过世了,内心有种谴责,好像没能做到一件该做的事,因此很想把这篇报道好好完成,无奈再次落版。
不幸丧生的青年是小生同乡,每天穿行长堤往返工作,还有一些令人感伤的巧合。小生不愿意解释为,受害者是外籍工人所以报道才被割爱。小生宁可相信这是因为《晚报》、《新明》已抢先报道了,造成失去新闻价值,才会被搁置一旁。现实终是残酷。
星期五还采访了一位青少年问题辅导员,缘因一则学生被偷拍到性爱短片的风波。老经验的摄影记者在一旁为两只菜鸟补充疑问,引发很多新的思考。类似事件,小生认为,无论多想责备这所学校的风气也好,都不应该过于注重性与当事人的身份。他们终须面对未来,那么做太不人道,尤其当他们都还是未成年孩子的时候。
经过几番周折,报道被要求悬置,小生认为是件好事。记者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发掘故事以提供娱乐?排列咨询来教育民众?还是寓教于乐?应该更多揭露上层社会的黑暗?还是去挖掘小人物的自卑心灵?
报章如果一直呈现上层结构的风光面貌,读者到底会氤氲出怎样的思维?中产阶级万岁。
3 October 2010
给个交代吧?
小生欠许多人,一个交代。
如果说这算是一种性格,大可称为劣根性。工作的关系,请朋友联络她的朋友,想做点访问,截稿了竟忘记给人家一个交代,的确非常不尊重对方。前两天都有大新闻,有不少临时的工作,同事都很热心帮忙,临了却没有说句谢谢,又落下许多交代。
主任问小生,为什么这么早到办公室,两点多就到了,是不是很stressed。小生说吃了午餐便过来了。Stressed以一个被动词性的压抑来诠释,在在比压力二字来得更有压力。香港巴士uncle说,你有压力,我都有压力。韩寒说,有谁工作不辛苦的。小生对这些都很了解,甚至都有准备,可就是血压降不下去,面对医生只是解释,昨天睡得太迟。他让小生哪天不stressed了再来。好,就定在那天吧。
毕业论文期间,小生悠游自在,如今只想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打电话去一些部门,说起英文硬邦邦,小生只想尽量不失礼就好。有时听同事电话访问,谈得真愉快,小生还没学到那种装熟的技巧。
写论文与写新闻最大差别是,叙事的次序,论文要按部就班,铺陈理论分析条理最后整理结论,新闻是抓住新闻点当头拍去,越是解释性的越给压后。小生死脑筋,怎么能忽略了过程?
小生接受了一项采访任务,认识了一群可怜的外籍劳工与学生,当然这种怜悯出自自我的主观立场。在新加坡,其实世界各个角落都是如此,外籍劳工,是最最边缘的群体。他们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丧失所有权力,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务必好好镇守不可随意越界,越界后可能就触犯了一些禁忌而遭禁闭或是遣送回国。
由于重大新闻的关系,这些客工被房东欺骗的故事只能湮灭,小生一开始真的很生气,这便是死有重如泰山,活有轻如鸿毛的可悲现实。有话不能说,小生当真欠下许多许多交代。
新加坡立法规定,房屋出租时,依据单位大小,即便最大的单位最多只能租给9个人。合法的处理,忽略地点优势,按市场价格大概一个人的房租最低是250至400元不等。一个外籍劳工,他的工资大约平均每月500至900元,合法的住宿规格,将使他难以应付新加坡的高消费环境。由于不熟知当地法令,很多人选择较便宜但不合规格的多人搭房单位(其实有时候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得过且过,相安则无事,倘若发生状况,被调查了,他们便成为牺牲品(因为屋主往往委托一个二房东代为转租,虽然收到的租金较低,但可以避免被查禁的风险,有事便推给二房东。而二房东则大量收租客,基本没有合约保障,或一次过收3、4个月的房租,叫那些学生以及劳工不能临时离去。所以只要一方出现问题,劳工的押金什么的都追讨不回来。小生遇到的这件,叫人心寒)。
只能这么解释,巨型城市(Megacity)需要太多廉价劳力,通过剥削他们来迎合社会的中间力量,也便是中产阶级(真他妈的就是我们自己!),因此中产阶级才买得到便宜的产品。为了迎合中产阶级利益,法律的制定有时候往往忽略这些劳动力,尤其当他们不是本国国籍的时候。这个灰色地带默默地存在,形成福柯所谓的隔离空间,以一种全景式监狱的规则牢牢监控着,嫌少出现在主流媒体就是要制造一种缺席感。因此,外来的劳动力无法合法地生活着,他们必须永远背负可能触犯法令的危险而存在,而巨型城市又不能失去这些劳动力,因此放纵资本家的剥削。
巨型城市一方面剥削他们,一方面仰赖他们进行硬体建设,却不愿意赋予他们适当的福利。如此嚣张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劳动力的原产地永远处于过量生产的境地的关系,劳工们也自我复制类似的认同,因此这些问题在资本社会永远得不到解决。
这算哪门子的交代!
如果说这算是一种性格,大可称为劣根性。工作的关系,请朋友联络她的朋友,想做点访问,截稿了竟忘记给人家一个交代,的确非常不尊重对方。前两天都有大新闻,有不少临时的工作,同事都很热心帮忙,临了却没有说句谢谢,又落下许多交代。
主任问小生,为什么这么早到办公室,两点多就到了,是不是很stressed。小生说吃了午餐便过来了。Stressed以一个被动词性的压抑来诠释,在在比压力二字来得更有压力。香港巴士uncle说,你有压力,我都有压力。韩寒说,有谁工作不辛苦的。小生对这些都很了解,甚至都有准备,可就是血压降不下去,面对医生只是解释,昨天睡得太迟。他让小生哪天不stressed了再来。好,就定在那天吧。
毕业论文期间,小生悠游自在,如今只想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打电话去一些部门,说起英文硬邦邦,小生只想尽量不失礼就好。有时听同事电话访问,谈得真愉快,小生还没学到那种装熟的技巧。
写论文与写新闻最大差别是,叙事的次序,论文要按部就班,铺陈理论分析条理最后整理结论,新闻是抓住新闻点当头拍去,越是解释性的越给压后。小生死脑筋,怎么能忽略了过程?
小生接受了一项采访任务,认识了一群可怜的外籍劳工与学生,当然这种怜悯出自自我的主观立场。在新加坡,其实世界各个角落都是如此,外籍劳工,是最最边缘的群体。他们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丧失所有权力,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务必好好镇守不可随意越界,越界后可能就触犯了一些禁忌而遭禁闭或是遣送回国。
由于重大新闻的关系,这些客工被房东欺骗的故事只能湮灭,小生一开始真的很生气,这便是死有重如泰山,活有轻如鸿毛的可悲现实。有话不能说,小生当真欠下许多许多交代。
新加坡立法规定,房屋出租时,依据单位大小,即便最大的单位最多只能租给9个人。合法的处理,忽略地点优势,按市场价格大概一个人的房租最低是250至400元不等。一个外籍劳工,他的工资大约平均每月500至900元,合法的住宿规格,将使他难以应付新加坡的高消费环境。由于不熟知当地法令,很多人选择较便宜但不合规格的多人搭房单位(其实有时候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得过且过,相安则无事,倘若发生状况,被调查了,他们便成为牺牲品(因为屋主往往委托一个二房东代为转租,虽然收到的租金较低,但可以避免被查禁的风险,有事便推给二房东。而二房东则大量收租客,基本没有合约保障,或一次过收3、4个月的房租,叫那些学生以及劳工不能临时离去。所以只要一方出现问题,劳工的押金什么的都追讨不回来。小生遇到的这件,叫人心寒)。
只能这么解释,巨型城市(Megacity)需要太多廉价劳力,通过剥削他们来迎合社会的中间力量,也便是中产阶级(真他妈的就是我们自己!),因此中产阶级才买得到便宜的产品。为了迎合中产阶级利益,法律的制定有时候往往忽略这些劳动力,尤其当他们不是本国国籍的时候。这个灰色地带默默地存在,形成福柯所谓的隔离空间,以一种全景式监狱的规则牢牢监控着,嫌少出现在主流媒体就是要制造一种缺席感。因此,外来的劳动力无法合法地生活着,他们必须永远背负可能触犯法令的危险而存在,而巨型城市又不能失去这些劳动力,因此放纵资本家的剥削。
巨型城市一方面剥削他们,一方面仰赖他们进行硬体建设,却不愿意赋予他们适当的福利。如此嚣张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劳动力的原产地永远处于过量生产的境地的关系,劳工们也自我复制类似的认同,因此这些问题在资本社会永远得不到解决。
这算哪门子的交代!
1 October 2010
入围与落选感言
明天是“第四届大马部落格祭”的颁奖典礼,配合亚洲部落格节在槟城举行,才刚开始工作的小生还真没办法请假。他们让小生写感言,既然是部落格的荣誉那就必须先放上来了:
“艺文”仿佛很高尚,其实仅仅是风格与形式的差异。
能够入围,那份虚荣感以及那种想要跟更多人分享的心情始终是一致的。
很荣幸也很抱歉未能出席盛宴,但,我原本就只是飘零在虚拟空间的一串符号,不如在那里相见吧。
谢谢。
由于工作的缘故,“宁致居”的篇幅好像越趋迷你,往往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当然,长篇阔论违背了网络快捷的原则,但小生还是很愿意充分地去书写。
昨天台湾时报文学奖公布成绩,马华作家大放异彩,想自己上个月连信都投不出去,当真有点抑郁,虽然知道自己的程度有限,但没能够正式被落选,就是不甘心。不知道梁实秋散文奖的那封投稿函送到没有,可快要公布成绩了。每到北国的夏天,小生便活在热切的期盼里。
5月中投的星云文学奖、八月底投的汪曾祺世界小小说大赛,也都落榜了。总有点落寞,但还是别太急的好。
都说了,“宁致居”是小生的写作练习平台,继续写吧,总会进步的。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