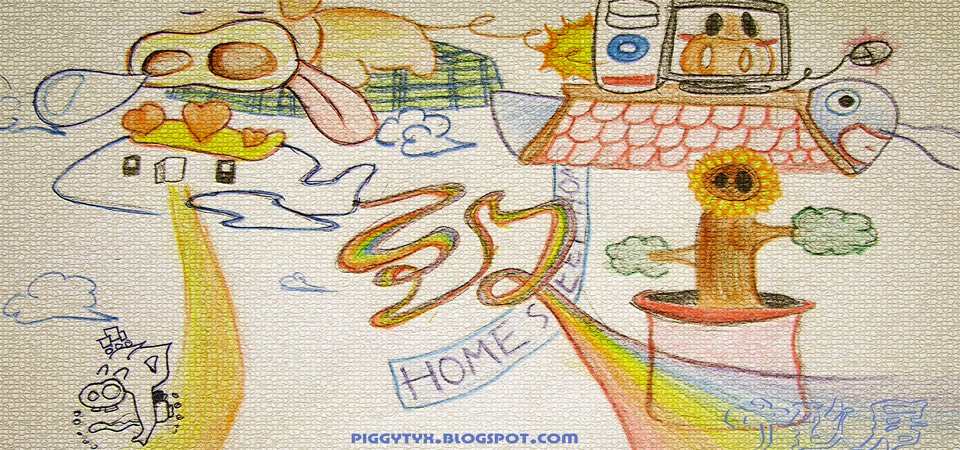多少次仰望漫天星辰,他都想搂着那位姑娘一同沉入梦乡。
三十多岁前他便几乎周游了世界,那一年他在货船上当二副,负责将船从一个港湾导向另一个港湾,当年红灯码头水浅,大船靠不得,货物都得搬上驳船,慢慢拖到码头卸货,哪里似如今这么先进方便。
四十多年后,他仍记得,七十年代初期在福建、汕头、上海等地卸货时,红卫兵跑上甲板,要船员跟着唱《东方红》;他记得迪拜当年的破落不堪与汶莱的富庶;他记得走下东非港口胡乱闲逛时沟通竟没有多大问题;他也记起他写给太太的情书,那些夹杂着中英文,陪伴他多少个漂泊日子的情书。他至今都还保留着。
我想,他一定很怀念那段远洋览尽天下风情的时光。那种浪游被系上一丝琴弦,偶尔被撩拨,发出柔美的轻吟,原来是家乡那位姑娘轻柔的发,仿佛一种被羁绊着的自由。
因为矛盾而美丽吧。
后来他辞掉工作重返陆地与姑娘结婚,生了三个儿子,如今各个少年才俊,大学毕业各自成家,我问他,他却回答,已经和妻子离婚,现在一人独居,老房子也卖掉了,新居里一个房间让出去,每月收租,老来不想闲着就这样开了近十年的德士,仿佛延续船员的日子,在马路上重新扬帆而行,一天往返几百里路。
说着说着,车子驶到了南大华裔馆,下了车,我始终没有问他姓名。途中我建议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他很是同意地一边开车一边转过头来,拍拍头说,要趁脑子不好之前好好记忆,我微笑说,一定没问题。
他的车子一直维持在一种和缓的节拍上,每个停顿与启动都极轻柔,像是几十年来对船与波浪的记忆,自然地调和了一般。
一路上他不时透过后视镜望我,我也倾前,双肘搭在前座的椅肩上,在他身后,我突然变得矮小,当年的他一定十分魁梧,在烈日曝晒的甲板上挥洒汗水,冲破多少波涛。每当黑夜侵袭,他便躲在微弱的灯光里书写一页一页的思念。思念随海波摇曳,不知道那些笔迹是否似他纷乱的心搏那般抖颤。
而他,始终是靠岸了,心却仍继续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