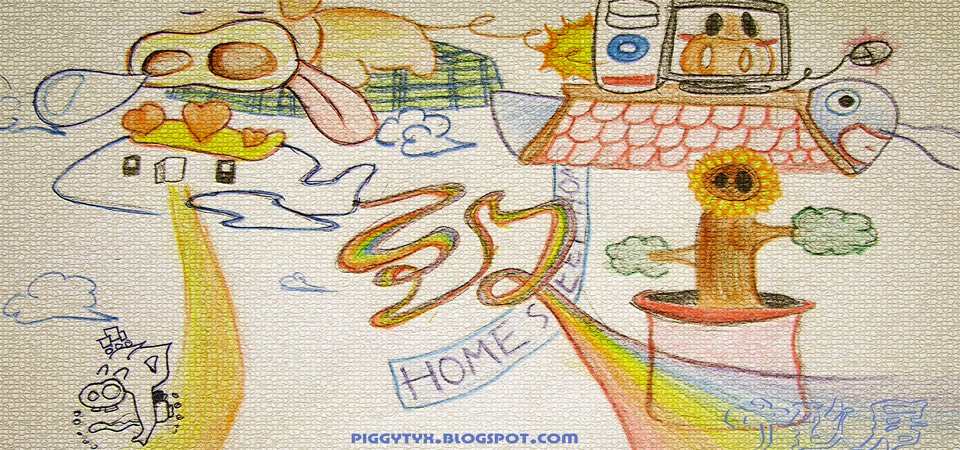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
自由女神站在东京湾上,目不转睛地眺望台场银光闪耀的楼台,女神一身纽约向洋的碧蓝,火炬燃着金色火焰,忽被一只乌鸦嘶哑的嗓音撕裂了没有云的天空,她栖在烈焰边,只剩下阴沉的轮廓,仿佛无名的黑洞突然被划开——“这女神的肚子好大”,同行的台湾友人说。
一
第一次到东京,一句日语也弄不清,第一顿晚餐,不敢走远,在早稻田市寒冷的夜中穿行。偶然邂逅吧台一样的拉面馆,进门一阵浓郁的猪骨香气暖滋滋地扑来,在投币机器上随便买了张票券,“Sorry, I can't speak Japanese.”
拉面馆的风俗,充沛的吆喝声,迎接相送,顾客临走前也要大声说“我完成了”(我是这般猜想的,后来才被纠正,原来是“谢谢招待”),把碗筷放上厨师台,拾起抹布轻轻擦拭桌面溅洒的汤汁——缘因那豪迈的嗖嗖声,粗面条窜入嘴时凌空弹跳的舞姿——我夹起面条放到汤勺上,噘嘴吹散蒸腾的白烟,顿一顿才张口把面吞下,混着一阵乱嚼,不敢发出一点声息,全然一个格格不入的旅人,啜着太浓太咸的猪骨高汤。吃完了赶紧潜逃。
东京的第一夜,我逃入被窝里,像一只雏莺嗷嗷待哺,但室内的空气很干涩,仿佛凝滞,期待着谁拿个什么来搅拌搅拌,我只好蜷缩着浅尝巴特神思中的恋人絮语,一阵晕眩,絮语变成咒语,头顶上的灯坠晃得厉害,这个适合幻想的城市,陡然虚拟成真,眼前尽是可以扭曲的光影与人形,另一度空间系谱。
“刚才是地震吗?”
“对呀,还蛮厉害的。”
“这是我的第一次。”
“真的吗?你好镇定哦。”
“是吗?”
“对呀,在台湾的话,好多人都要尖叫了的。”
电视台很快广播了地震的消息,震源在静冈县,东京感受到5度的震荡,我不明就里,只好将5度当作中庸的表达。电视台24小时都在发放消息。
二
那些画面历历在目。乍看只道是三维虚拟,黑色的巨浪吞噬村庄农田,摧枯拉朽。镜头很远,黑水仿佛是岩浆,粘着地匍匐前进,所过之境,有东西熔化了,有东西着火了,黑烟奔腾,有米粒般大的车子在移动,人显得过于渺小,像笨重的尘埃粘附在土地上——庞贝城——这时,虚构与真实取消了界限,我们阅读过太多电影,画面与画面交叠,一张多重曝光的底片,苍白得已然不知自己的恐惧到底是源于自身积累已久的,对毁灭的虚拟想望,抑或是借电视卫星直播所目睹而产生的,同步的震撼与颤栗。
现场直播“Live”,倒装就变成“Evil”,由恶魔来伪装。
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我们在万水之遥的南洋收看新闻转播,早稻田大学的千野教授电邮说东京基本平静,研讨会绝不取消,一定照常举行,我依旧乘搭15日的班机飞往东京,在亲朋好友的劝解下,一往无前,竟有慷慨赴会的激情。到底是什么促使我前去,我至今仍不明白,竟还奢望富士山下眺望雪景的自然幽静,以及满园粉红的樱花春景。或许太早了一些,东京还是0度的空气,唯我踽踽独行。
“不要相信学者的坚持。”我对同屋的朋友说。临走前。
无法睡眠的七个小时飞行,我被困在瓦砾堆里,挣扎着动弹不得,没有人发现我,全世界都被掩埋。我的手紧握着手提电话,想捎最后的一封简讯给我最爱的人,可那人始终没有浮现在我的异想之中,我不知道她会是谁,拇指却机械般开始敲击键盘,屏幕发狂地亮起来,在无尽的黑暗里耗尽所有能量,却没有只言片语。我发誓我不曾睡眠。
我断断续续看完了电影版的《挪威的森林》,想着为什么要删去小林绿要求“我”一定要以她为性幻想对象的那句对白,而后“我”也没能在电影里完成自慰——这如此重要的仪式,更没能在观火的颠覆中亲吻绿。
绿可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我带着遗憾下了飞机,迎接我的是核电厂再度爆炸的消息。
于是我拾起口罩,在东京的第一个夜里,企图过滤一切恐慌,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满喉干涩地醒来,疼得无法吞咽唾液,我努力咳出一口稀稀的透明的痰,当中有小小的血斑。我理性地解释那是因为气候干燥喉咙内壁裂开所造成的结果(绝不是甲状腺突变!),但我仍不禁确信我就快要死了。我仿佛能够看见体内细胞变异的那种没有规律的原始舞蹈,以及异变的狂喜表情。我坠入无尽的神话,幸运的话我将变成超人、蜘蛛侠,但我却始终沮丧地认为我将死去,或变成一个濒死的,恶魔的絮语。
三
我和台湾友人结伴走入东京湾的一片清寂,海风让空气变得愈加湿冷,友人说:
“可以听见海的声息。”
“嗯,以及波的罗列。”
“波的罗列。”
从未想象过城市与沙滩可以如此紧密相依,东京湾不可逆转的弧度架着先进的大桥,银色的大厦将阳光拦截在海湾的瓮中返照水面,潋滟水光中却冒出一个古意森森的暗褐色锥形砖墩,斑驳着青苔,顶着一盏灯,大概夜里用来照明,方便测量潮汐涨落。
我们见到零星来散步的人,有位大婶卧在步行道上仰望晴天,晒太阳(我敢保证她不是被辐射熏昏了),还有一位穿着运动装的女子牵着小狗,小狗穿着裙子。小狗冲着鸽子奔去,溅起群鸽乱舞。那天,阳光恰到好处,氤氲几许温存,水鸟浮在浅滩上,此外还有几许沙洲,落木残叶,一脸冬末的倦怠,教人好想赖床。
俄尔有直升机从头顶掠过,失忆的人瞬息重拾地震、津波以及核子危机的恐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属于东京的空气。
四
服务员各个笑容腼腆,遣词温柔,总是躬身侧耳倾听顾客的询问,我不敢直视,深怕暴露自己旅人的身份,因此便猜不透那谦慈与笑意背后,天灾人祸的惶恐与敬畏,如何在他们心中制衡纠结,但我始终相信,生活是不得不延续下去的必须。与其惊慌失措,倒不如继续生活来铭记自己的存在。
核危机爆发的第五天,我们走在涩谷街头,流行的素色冬装点染市景,像一幅泼墨画,人潮恢复了,我们开始购物,开始寻找美食,尽一个真正庸俗旅人的本性——我应该携带一种怎样的情绪?我只是一个游走在灾后东京的旅人,没有踏入灾难的中心,在濒临毁灭的边陲徘徊,想象自己陷入囹圄,或是只能透过电视转播去捕捉那些面孔、泪水以及真实,对真正深陷苦难的人而言没有半点意义。
五
如果冬夜,一个旅人,如我,迷失在早稻田市的街衢之间,诚惶诚恐不敢问路,兀自摸索,或许一辈子将走不出来,变成一个寄宿的游魂。在东京度过的五天里,每一个清晨都是一场新的叙事,我不敢说这是一场纯粹的错乱,但处在这般非常的时空里,人事物纠结到一块儿,没有什么比这更摸不着脑袋的了。母亲甚至害怕来电,必要每天透过姐姐的转述来搜集我的消息,我也每天一次在面子书上描述此时此地的情境。就说,学术研讨会的讲者半数缺席,都以安全为由,结果会议浓缩在一天内结束,我们歇斯底里地要求教授协助更变机票提早回国,机票确定后,我们却又舍不得离去,并珍惜每一个散步的机会。走累了,回到睡房也还是硬要泡上一缸热水澡,奢侈地让心平静地沉下。而后我因害怕错过班机选择到机场去过夜,成夜躺在那个巨大的冰箱里,保鲜我的记忆。多少件衣服都是虚设,踱步、三不五时上洗手间、神经质地从地上弹起,到处都是发狂的冷空气往我身子里钻,贪婪地吮吸我最后的热情。
回程的飞机。我竟然开始期待另一个小林绿的出现,就坐在我身边,我们彼此间没有沟通上的不便,她是一个可爱的日本女学生,单纯却又充满傲气,就像真正的绿一样。期盼在飞机宣告起飞的那刻正式终结,我的左边是一张折叠齐整的被子及白色枕头,右边是通往青空白云的窗子。空中小姐来来往往,端上餐饮时日航空姐会穿上花围裙,她们殷勤地问我要不要续一杯茶,我却点了ASAKI啤酒,粗野地饮尽,偷偷打几个空虚的嗝。
六
研讨会举行之际,余震再度光临,早稻田文学院轻轻摇摆,像一个戴耳机听蓝调歌曲的少年合眼时的基调。我在机场闲晃时也感受到微乎其微的震荡,感觉光影有点凌乱,不过一切安好,收银员没有少找一分一毫。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昏眩一直持续至今,偶尔诱发极细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反胃,迷离却不欲作呕。
大概,不是辐射的关系。
(原载《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1年0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