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沒有一點傳媒訓練便加入新加坡《聯合早報》,在采訪組充數當記者。那時候的主任新慧姐安排我到意外組磨練磨練,第一個星期就被天明老大罵了好幾回。我的第一個署名報道,紅燈區芽籠發生的一起離奇車禍,德士深夜沖入五腳基,撞死越南女子。事件次日的跟進做得慢了,又被老大一頓臭罵,連攝影同事也沒有安排,自己一個人慌慌張張搭德士到事發現場,看工人修復柱子崩裂的危樓,一边向主任匯報,被問到拍照了沒,才又趕緊打電話請攝影組幫忙,臨時調了同事紫薇過來支援,那樣一個夜晚。有種菜鳥式欲飛無力的喪氣感。
後來漸漸每天早上從殮屍房的眾生相中學習到和人打交道的一點一點技巧。比如要如何委婉地從傷心的死者親人口中了解來龍去脈了解死者其人,如何平息他們因悲傷而起的對媒體的憤恨,如何保護自己不要和激動的家屬糾纏,如何穿梭於敵對的棺材佬間套取一點一點有用的情報,如何穿梭於相互競爭的報章記者之間,以及如何不要驚動負責警官,免得警官勸誡家屬禁口而白費了努力。
意外組的同事逡巡於那扇宣判生死的門前,為死者作傳,為生者傳達哀思,但有時候可能處理不盡圓融,我們被質疑被唾罵,像一群卑微的惡戲的多事的長舌的惡魔,人人得而誅之。
其實至今,我仍不習慣到靈堂采訪,那個氛圍,那個本該只屬於親友為往生者送別的空間,置身其中,總覺得自己像一顆走錯棋盤的黑白子,無論多努力掩飾,總與那人間悲情格格不入,甚至是一種意外的褻瀆。多少次,被那些雙眼失神的家人歇斯底裏地逐出靈堂,如此狼狽,但有時候竟甚至因為被罵被逐而感到某種慰藉,暗想本該如此,本該如此,能否痛快毆打我一頓,方能解除心中莫名的罪惡感。但也正是在這種劇烈的摩擦與震撼之中,才漸漸摸索出社會新聞的價值與意義,原來呈現一場意外悲劇,彰顯死者曾經的存在,除了吸引讀者目光,更可能有助於避免下一場悲劇的發生,並不僅僅是消費與被消費的惡性循環。當然有時候適得其反,如自殺事件的曝光,惹來仿效,像一枚不可碰觸,禁忌般的骨牌。
除了那扇審判生命之門,生命終結的現場更教會了我許多事,耐心、巨細靡遺,與其做撒網的漁夫,不如當個沈著的垂釣者。因警方辦案而被誇張地封印起來的命案現場,記者總像是被結界隔離的魔獸,逡巡結界之外,渴求每個蛛絲馬跡,嗜血的蝙蝠。那年,一個年輕女傭天還沒亮,把患有小兒麻痹癥的小女孩拋下樓,我們趕到現場,街坊鄰居三五成群地議論,整座組屋被封鎖,我們只能在組屋四周徘徊,尋找關於死者的情報,從你一言我一語中慢慢拼湊。突然有記者動起來,大家像受驚的貓鼬往同個方向奔去,那裏有一對貌似小死者爺爺奶奶的老夫婦正走出組屋,他們走得很快,可能是被我們逼急的關系。很菜的我跟上前,聽其他記者追問他們問題,老人只是低頭不語,攝像機劈劈啪啪貪婪地攫取這一幕又一幕情景,電視臺攝影師抄到前頭,什麽也不顧,倒退著走,只管把鏡頭對準兩位老者,我們竟這樣無從溝通地移動著,語言完全喪失功能。
這三年裏,總是在一個又一個現場裏等待,扮演守株待兔的獵人,當一頭潛伏草叢的黑豹。
我還記得小女孩的樣貌,白白的臉龐,濃濃的眉毛,攝影記者相機裏有許多無法公開的照片,在那裏,小女孩倒在草坪上,睜著眼,失卻表情,雖然從高樓墜下但看不見血,卻也正因為沒有血,而更讓人沈痛,生命竟這樣沒來由地被終結。
社會新聞瑣碎,卻關乎個體的存在與消亡。我始終無法舍棄心中那種尷尬與畏懼,面對死者、受害者的親人時,總戰戰兢兢,我不曉得自己是不是給他帶來了二度傷害,但我知道身為記者,當這件事關乎公共利益,就必須去寫去面對。但吊詭的是,我們卻又很難評定怎樣才算關乎公共利益,永遠沒有一個標準可言,有時甚至淪落為純粹的報章銷售利益。
三年間,網絡媒體發狂延伸,那些無處不在的眼線,讓更多單純的事情成為你一言我一語的公共事件,有些芝麻綠豆的小事也成了社會輿論關註的對象,我於是開始懷疑,到底誰才是主流媒體,誰才是邊緣的聲音。而印刷媒體的沒落也催逼著我質問自己,到底我寫的新聞是寫給誰看,答案卻永遠模糊曖昧,總之是有人看吧。如果沒有人看,所謂的公共利益又是什麽,堂而皇之去采訪那些新聞事件的理由又是什麽?可能剝光了外衣,什麽也不剩,噢不,可能還有蚤子。
最近,一位德士司機問我,如果有一個事件,一旦報道,天下必定大亂,我會不會報道。我略作思索,說,會的,但還得先判斷。他繼續追問我,如果我身邊的人會因此受傷,我還會選擇報道嗎?我稍微遲疑了一下,還是說,會。然後車子到了目的地,我還錢下車,他說很高興和我聊天,我也向他道了晚安。
這不是一個簡單可以概括的問題,當中牽扯太多道德和倫理,以及每個事件發生時的綜合判斷,永遠無解,但或許任何抉擇都值得批判吧。
剛到報館不久,當時的意外組主任詠梅給了個任務,到讀者舉報的情色按摩院當臥底。頃刻像是男記者要納投名狀的姿態,獻出第一次,一往無前,可是膽小如我,竟先花了一天觀察按摩院四周的情況,第二天才在攝影同事麒麟的陪伴壯膽下走進黑玻璃裡的按摩院,而他在門外伺機拍照。
付了半小時的按摩費,一個年近三十的女郎把我接到後房,狹小的房間只容得下一張床,合成塑料制成的薄薄夾板隔著另一個房間,我脫了衣褲裹上毛巾,緊張地趴到床上。女郎高瘦,穿著並不暴露性感,窄裙高跟鞋,我不敢多看她,實在記不起她的樣子。她倒了些精油,塗抹在我背上,沒有半點勁道,我盡量不說話,怕泄了底細,但女郎很自然地和我攀談,我只能勉強一句一句接話,才沒多久便問我要不要特別服務,一如讀者給的情報,我只好裝傻說自己只是個誤闖的遊客,不知道什麽是特別服務。女郎很和氣地解釋,就是打飛機口交什麽的,一次多少錢多少錢,平和地朗讀著菜單那樣,語氣裏沒有什麽不妥,自然得宜,在那樣一種氛圍裡,秘密寶盒般的空間裡,似乎合理過了頭,而我心跳狂躁地刺痛著思緒,不知該怎麽整理嘴邊的話,結結巴巴地拒絕說,沒想過,怎麽怎麽會這樣……還是不要啦。
女郎告訴我,每次按摩費自己分不到多少,只有靠特別服務給自己賺外快,似是有點央求的意思,我只擔心會不會被識穿,頭也不敢擡起,埋在手臂之間。她見我不願消費,雙手在我背上胡亂摩挲,沒幾分鐘,問我能不能提早結束,外面還有客人在等,及早結束了那尷尬而緩慢粘滯的時光。我慌亂地竟把衣服穿反,走出去,管賬的中年婦女喲一聲,我只得紅著耳根到廁所更換,聽她對女郎說,“瞧你把他吹的!”接著一陣陣訕笑,特戲劇化的場面。
新聞見報後,警方的確去掃蕩了,為此還得訪問周邊商家,問問意見,做個跟進報道,卻被一位大叔臭罵,讓我警告那個寫報道的記者,人家明裏暗裏做了什麽,無非為了糊口養家,也不至於傷天害理,那個報道就這樣毀了一個女子,還有一個家庭。我不知道該怎麽辯解,當然可以說,情色行業養肥了老鴇,也間接破壞別人的家庭,那些女郎不也都是受害者,我的所作所為倒也算是一種救贖吧?仔細想想,卻又為何受懲罰的不是那些嫖客,而只是一批又一批的女郎。我的努力仿佛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一場演出:這裏有人暗操醜業,記者揭發了,警方順利搗破淫窟,之類的戲碼,恍如一場喧鬧而已。
或許我不適合當記者,或正確說,不適合當采訪社會新聞的記者。我的懦弱與優柔總影響著我手中的筆,影響著語詞的選擇,行文的方向。某天下午,各報記者都聚集到某醫院的加護病房,那個慟哭的媽媽失控地咒罵著,被家人攙扶勉強才能行走。病房裏躺著二十歲的小伙子,一動不動,仿佛病房裡凝凍了時空,唯有心跳儀屏幕上的小綠點在波動。偌大的病房客廳,除了哭聲,便是一張張沈肅的臉,記者們不禁也皺起眉頭,盡可能小心翼翼輕聲地試著與那些親友談話。我趁那爸爸落單時湊近問他,事已至此還有什麽打算,謹慎地選用詞匯和語氣,盡可能顯得莊重,他看著我,濕紅的雙眼像是在回答我的問題,卻始終沒有說話。
小伙子遇車禍腦死,根據法律條款,醫生可為腦死病人拔管,只要病人生前沒有選擇退出,便自動成為器官捐贈者,醫生可按情況進入器官捐贈程序,但於家人而言,心臟依然搏動的孩子,還有體溫的孩子,怎麽能說是無可挽救的生命,怎麽能不再努力任死神擺布,怎麽能活生生剖開孩子的肚皮取走那些依然搏動的器官?那媽媽悲慟地嚎叫,以一種超越哭的聲響震碎整座醫院的寧靜,震碎每個人心裏最後一道防線。
晚上八點,醫生進行拔管,親友匯集到床前送別,我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站在病房外,目睹那裂人心扉的儀式,用那媽媽的話,那是親手殺死孩子的儀式,但在法律條文面前,無人能豁免,仿佛一場早有結果的審判,只要符合條件,一切變得理所當然,沒有商量的余地。而在人性面前,我們又剩下些什麽?一個普通民眾能怎麽抵抗那無形而又無所不在的威權?
我們冷酷地站在病房外,見證一個母親的掙紮,聽她聲淚俱下,崩潰,失去理智,發狂,一聲聲對天發問,而答案呢,答案並不在風中蕩,唯有加護病房裏彌漫著濃重藥味的玄迷而已。
她像面臨海嘯時螳臂當車那樣渺小而無力。
記者荒謬地闖入那場域,竊取所見所聞,在截稿時間的催逼下,寫成千多字的文章,一邊下筆,還要一邊控制自己,不能太過煽情,要平衡各方的說辭,謹慎地選擇新聞照片,選擇敘事角度,但無論如何,這一切怎能不煽情?即便把所有形容詞都刪掉,事件本身即是煽情,而煽情又有什麽錯?於是我最終好像是惹了麻煩,隔天勞煩同事再寫一篇立場更中立的報道,才算告一段落。而最讓人郁結的是,醫生最後竟說檢查發現小伙子的器官不適用,沒能成功捐贈器官,仿佛之前一切掙紮與苦難到頭來只是一場玩笑,那些所謂死者捐贈器官能營救更多生者的豪言壯語頓時顯得毫無意義。
寫到這裏,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麽結束這篇文章,畢竟三年太短也太長。很短因為它瞬息而逝,沒有重來的機會。很長,就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點點滴滴如一棵棵枝節繁茂的大樹無限勃發,足夠我追憶一輩子。
踏出大學的第一份工作,這首三年賦予我的,就像少年時對校園生活最單純的向往,每每在體制嚴明的校園裏追逐任何叛逆的可能,故意總在上課前打球,汗濕那純白的校服,一上課就埋首睡覺。感恩初為記者的三年,能夠以一個社會新聞記者的身份,著眼於瑣碎的關於微小人物的故事,親手摸索這座島國的每一角落,但有時候卻感到痛苦,納悶自己怎能如此深入這座城市,卻竟對自己一海之隔的家鄉——新山——毫無認識,即便我再頻密往返這兩個地點,仿佛都無法逆轉這局面。我卻又始終倔強不願意申請永久居民的準證,自豪地稱自己外勞,幻想以永遠的離散抗拒城市的召喚,冀望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能讓自己看得更透徹,無時無刻錐刺著自己,提醒自己絕不可變成麻木不仁的寫字機器。
謹以此文,告別意外組,告別三年的社會新聞採訪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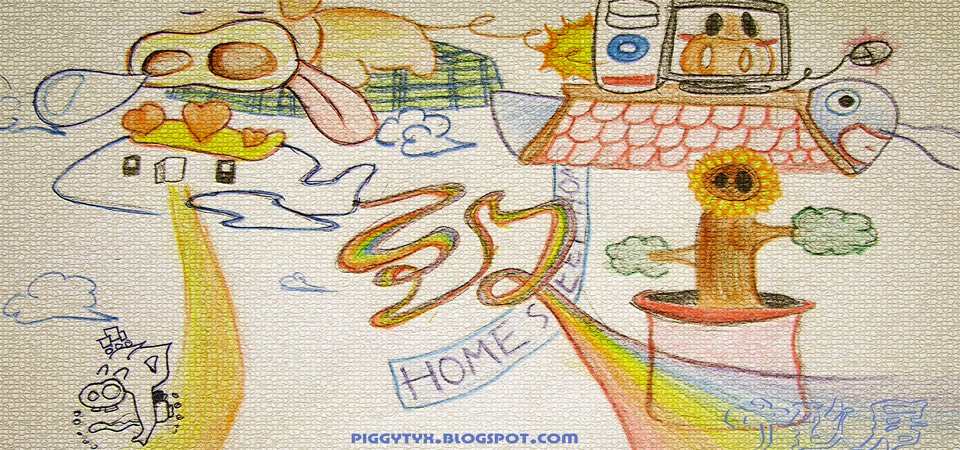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