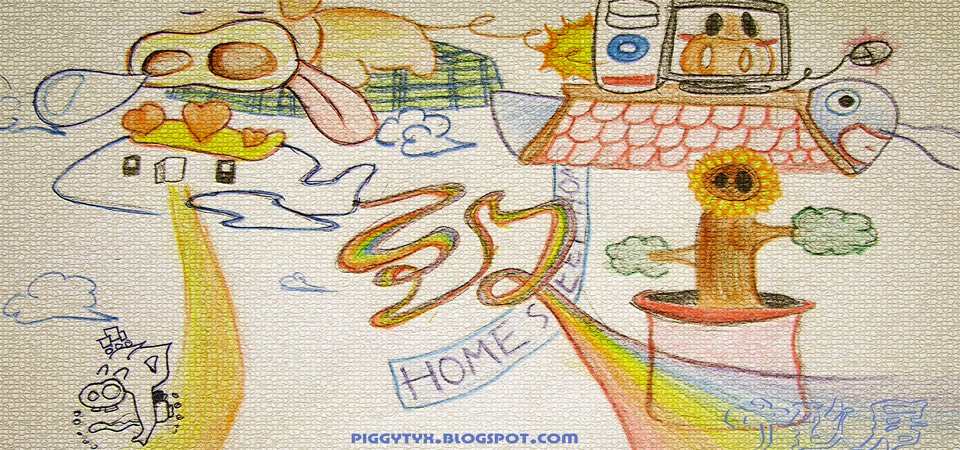演唱会中午,宽中前面那条窄窄长长的海滨马路往公主湾的方向局部被围了起来,工人缓缓铺盖新柏油,车龙塞得老长,还碰上了宽中上午班放学时间,差点就没能把车开入宽中山门的坡道。
而又同乐会结束离开校园时,马路已铺好,开着车子,才又发现海峡上远远停着六七艘巨大的填土船,正把宽中风帆队徜徉的那片金色海洋包围起来,我转过头,跟乐乐和阿桂说,可能二十年后,我们就要以更年长的团友的身份,跟合唱团的学生说,以前学校可是背山面海的呀,以前那个时代的学长姐,可是凛着海风,所以有了《海》和《海峡的风》这样的诗曲创作。
就在“绽40”庆典,我们热烈追忆的时候,熟悉的记忆图景正悄悄变更。
要如何抵抗这些变化呢?或许依然还是要靠大家眷眷于合唱的心吧。参加合唱团后,总是对和声极其敏感,听到有合唱的歌声传来,便心痒痒要一探究竟,犯瘾一样。于是当联合大合唱的消息发出去,各代团友很快就把名单写得好长好长,从1970年代毕业的团友,到去年刚高中毕业的新新人类,因为喜欢唱歌,这样单纯的想法,让超过四十年跨度的世代,在四个月内的五次联合练习里,寻回了那熟悉的默契。
第一次的星期天大联合练习,在新山宽柔校友会店屋二楼的会所,大家直把场地塞满了,台阶整齐放着一对对大小款式不一的鞋子,三台冷气机完全抵挡不了大家的热情。我记得当《星夜行程》唱响时,男低音成熟的厚实感让地板都震颤不已,到了正式演出那天,脚下的站台像是我们的琴箱,每一个“Rom”都是一次剧烈的震撼,这或许正是陈徽崇老师创作时所要表现的效果吧?仿佛脚步声,急缓交纵在星空下行进,一如他对音乐与新山这块土地的理想,总是踽踽独行,虽千万里吾往矣。
因为伟吉的提议,六人重唱小组又聚在一起了。高一刚进团那年,听他们几个唱King’s
Singers的“Lonesome
Road”,和声太美了,总有点嫉妒,所以到了高二高三,校内重唱赛时,就到处揽人组队,唱“Flying
Without Wings”,“Goodnight
Sweetheart”,《可爱的玫瑰花》这样讨喜的歌。也是那时候,六人小组选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啦》,缺一个领唱,立彬把我拉了进来。毕业后,人员变更扩大,组了一个“昕达龙源宏窦彬豪”超奇怪名字的组合,但很快又因为大家忙学业事业各飞东西了。直到“绽40”这样的机遇,还有伟吉的提议,我们又聚在一起了,立彬、亿达,加上锦淞、子康,再次回到六个人的编制,再唱一次King’s
Singers的歌曲,像是重现了当年那几个毛孩对重唱小组音乐的天真想望。
“Londonderry Air”来自爱尔兰,“Danny
Boy”是歌曲的俗名,这次我们把自己称作“Danny
Boys”,一如那歌词意指的,有种离愁,以及亲人声声温暖的讯唤,教我们要懂得珍惜所有相聚时光,要懂得回家。而唯有通过歌唱,才能解这乡愁,我们对合唱的乡愁,多么契合这样一个日子。
看着台下满座的观众,台下前排是谢校长、胡老师、树奇学长、恺莉……越过第四五排后就是黑压压一片了,深吸口气,二楼的座位也几乎被填满,立彬掏出音笛给了升F和升A,我们先哼一哼确保无误,并肩站好了,对视,呼吸,身体跟着吸气而扩张抬高,随着微点的下巴,唱出第一个和弦,“O
Danny Boy”。那和声圆融,像是在周身荡漾。包裹在乐音如海洋深沉缓慢的暗流,控制室给了我们蓝紫色的灯光,越是变成那片海洋了,可以悠闲地徜徉,把每个挂留音清晰交叠缓解了,最后舒服地终止在E大调澄亮的和声中,有泛音飞扬到礼堂的顶盖去。
演唱会当天一直在换服装,从Danny Boys到上半场的联合大组,到下半场的JBCC,还有最后的联合大组,都没时间好好和许久不见的朋友寒暄,结束了又假装责任心地开始收拾,却又一心想着和大家合照,一分心两边都不讨好。总是如此。
十年前的“绽30”,我们还是学生,一年里准备了合唱团三十年的经典曲目,像《海韵》《拉纤歌》《八骏赞》和《星夜行程》,每一首都是大块头的歌曲,由青涩的十多岁少年少女演绎,有时要刻意变得深沉,唱得背脊抽紧,双手发抖。十年后,集合百人团友,再唱陈老师的作品,对大马现代诗有了更多理解,对音乐也有更深的体会,当每个人如此细微的成长汇流成和声,那效果是何等动人,即便是多年没有歌唱了,仿佛心中也有某种不能名状的东西被唤醒了,像花一样绽放。